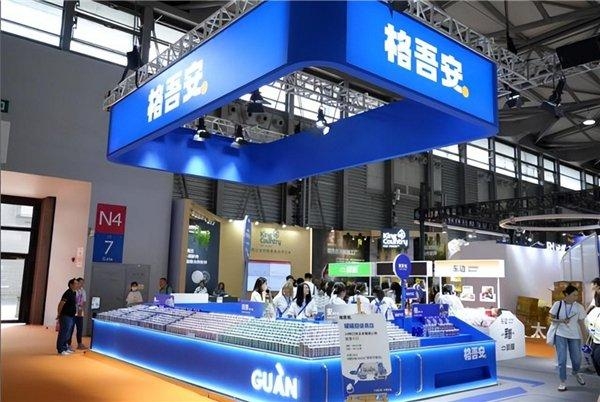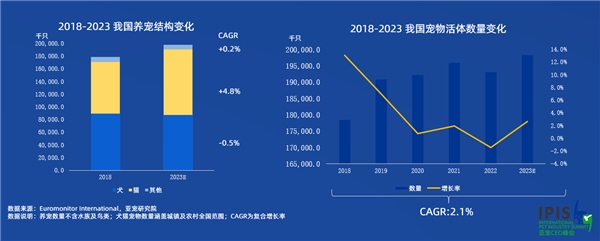最近,如果你向我所在的大學宿舍樓道隨意扔塊石頭,很可能會砸中一只“狗”。
別害怕,它不會叫,不掉毛,不拉屎,還非常環保——同學們使出渾身解數,把快遞紙殼箱回收再利用,手工打造了專屬寵物。他們真情實感地愛護它,跟它說話,喂它狗糧,用繩子把它拴在宿舍門口“站崗”,甚至帶它出門遛彎兒,游蕩在“狗”山“狗”海的操場相親角,像所有操心子女終身大事的父母一樣。
這事本來也不新鮮。2020年,英國一50歲男子和妻子養了一只“紙狗”當寵物。夫妻倆住在只有一間臥室的公寓中,覺得養一只真狗對狗不公平,于是就用紙板做了一只假狗,還配有紅色項圈和專用遛狗繩。
養狗,作為一種“非必要”項目,眼下正成為一些大學生的生活“必需品”。在多地新冠肺炎疫情反彈、學校封閉管理的情況下,年輕人被核酸、口罩和健康碼困在宿舍里,缺少真實的社交場景,紙狗卻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近了。幾乎沒有大學生能對這股養寵大潮無動于衷。
我的朋友圈里,經常有人贊美走廊偶遇的、造型別致的可愛紙狗,或譴責棄養紙狗的“喪盡天良”。連宿管阿姨也配合“演出”,提醒同學們:白天盡量把看門狗或其它動物牽回寢室,晚上再放出來,以防保潔阿姨拖地時弄濕弄臟。我覺得這個“牽”字用得極好,它充分表達了阿姨與我們的共情。
每一只紙狗,有獨特的主人,但所有的紙狗,都被賦予了一種共同的寄托——養紙狗者不是“瘋”了,而是在遵守防疫政策的前提下,小心翼翼地守護一份“日常”。在特殊時期,這份“日常”格外珍貴。
2019年,我上大一,大學時光幾乎與疫情重疊。有網友說,點擊查詢我們這些大學生的精神狀態,“瘋”是顯示結果之一。理想中的大學生活,是學習知識、開拓視野、旁聽感興趣的課程、參加喜歡的活動、交到更多的朋友。現實中的大學生活,要上網課,忍耐封校和核酸,對抗內卷。憋悶的時候,一只紙狗,是個出口。
上網課期間,我們在洗臉盆里學游泳憋氣,冒著被鄰居投訴的風險練習散打拳擊。隔著屏幕、倒著時差朗誦詩歌和表演話劇,對著雙機位攝像頭完成試卷習題。有的同學、老師,4年來甚至從未見面,來不及創造回憶,就在云端的畢業典禮上匆匆說了再見。
等我們好不容易回到學校,又得時不時面臨封閉管理。和舍友的關系是親密了——不親密也沒辦法,天天在十幾平方米的空間里,大眼瞪小眼。憋得久了,有人和舍友手磨豆漿,并成功弄出了腐竹皮。有人摸著室友和自己的身體,學習系統解剖學。有人沒事就想嗷嗷嗷地吼兩嗓子,聽最“燥”的搖滾樂,宣稱“發完顛后,精神狀態會好很多”。
在這一大片場景中,養紙狗算是“正常”的。
看上去,這事兒透著點幼稚和傻氣,卻能讓我們有些鈍化的感受,重新變得生動。和“狗”打交道,我們變得更關心“人”。狗是假的,但人與人的聯結和回憶都是真的。在內卷錦標賽里,我們狗頭貼狗頭,彼此欣賞,握手言和。
曾經“阡陌交通”的“雞犬相聞”,上傳到了互聯網,就變成眾狗的爭奇斗艷:中國人民大學的電鋸惡魔“波奇塔狗”,華南農業大學的“185體育生狗”,四川大學的“狗”,華中科技大學的“狗”,中國美術學院的“狗”……大家沒能去看看彼此的校園,但卻在“狗”身邊,達成了某種精神共識。
狗也像一面鏡子,一個提問。想想那些現實社會中被迫宅家、滿地打滾甚至暴躁拆家、發泄精力的真狗,那些新聞里被奉為網紅、戴口罩做核酸的真狗,那些被違規執法的防疫人員棒殺的真狗吧。
巴金寫過一篇《小狗包弟》,“不能保護一條小狗,我感到羞恥”。狗的命運,也折射出人的命運。關于疫情防控,中央三令五申不能違反“九不準”,但還是有地方層層加碼。一只狗的死去,和一個人的逝去,都值得深刻反思。
紙狗臉上,掛滿了年輕人的苦笑,紙狗用沉默代替狂叫。這些,都是我們對“日常”的呼喚。就像《小王子》里提到的那樣,狐貍提醒小王子,“要永遠對你所馴服的一切負責”。養狗-哪怕是紙狗,一樣意味著對另一個生命負責。
我們時刻準備著。
王子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