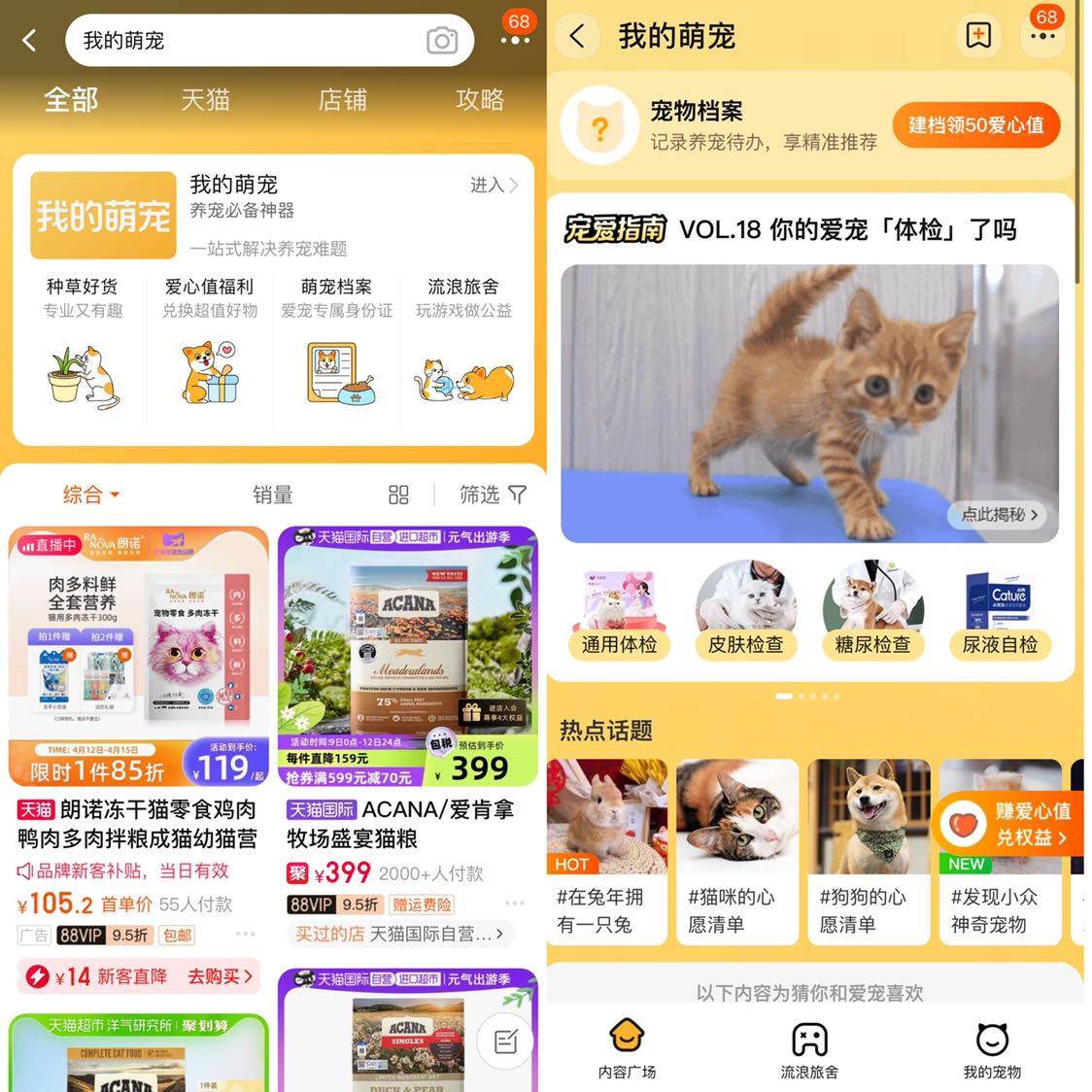我宰過一只鴨子,還是一只瘸腿的鴨子,這件事讓我至今難以釋懷花貓的小屋 余虹。
也不知道我媽是從哪兒撿回來的這只瘸鴨,我媽看了我一眼,低下頭輕聲輕語地解釋說:也是一條命花貓的小屋 余虹。
我愣愣地盯著這只黑不溜秋的瘸鴨花貓的小屋 余虹,它也可憐兮兮地抬頭瞅著我,同時抖動著瘦弱的小身子。
我媽又補了一句花貓的小屋 余虹:咱們吃不了的飯菜,剩著也是剩著。
我嘆了一口氣——唉,拗不過我媽的仁慈,我只好妥協花貓的小屋 余虹。
再說了,我也不敢保證能囊括家里的剩菜剩飯,為這事兒我媽也沒少嘮叨我。
我無可奈何地扔下一句話:好吧,只要它不會鉆進我的房間。
聽到這句話我媽很高興,接著很快就行動了起來——她先給瘸鴨的傷腿敷了些藥,用紗布細細地包扎好;然后很小心地喂飽它,最后又用小刷子就著溫水給這只瘸鴨洗了個澡。
接這樣,瘸鴨漸漸恢復了生氣,至少它不抖了。
瘸鴨不抖了之后,就少了些畏縮,多了些膽量——吃飽之后在家里溜達爽了,就會抖擻起精神“嘎嘎、嘎嘎”地叫上幾聲,聽上去很煩人。
偶爾瘸鴨還會一歪一歪地踱進我的房間,見我隨手扔過一個殺傷性物件,便又“嘎嘎、嘎嘎”地啞叫幾聲,一歪一瘸地逃去......
我媽在閑暇時很喜歡逗弄這只瘸鴨,看得出來,她能從這只瘸鴨身上獲得一些快樂——每每忙完家務,我媽總不忘喂飽它;聽見飽食后的瘸鴨沙啞地“嘎嘎、嘎嘎”幾聲,我媽就會微笑著撫一撫它的腦袋。
于是,這只瘸鴨一天天地肥胖了起來,腿似乎也不那么瘸了。走在家里總是昂著頭,“嘎嘎、嘎嘎”地叫幾聲,把不給它讓道的人嚇一跳。
我就更覺得它礙眼,尤其它越來越多的“嘎嘎、嘎嘎”聲攪得我心煩。既然它已經長肥了,我還看中了它的肉。
終于有一天這只瘸鴨在我的房間里賴著不走,還“嘎嘎、嘎嘎”地叫個沒完,我就一把揪住它,跑進廚房操起菜刀,嘴里嘟噥著一句最后給它的解釋:“瘸鴨瘸鴨你莫怪,你是盤里一道菜!”
“咔嚓”一聲手起刀落,瘸鴨被我干凈利索地斬首——它撲騰了幾下,最終伸直了那條從未伸直的瘸腿。
倒上開水浸泡,眼見著快要拔盡鴨毛時,我媽從外面回家了,發現了即將被開膛破肚的瘸鴨——而我媽的手里,還拿著買菜時專門給瘸鴨撿的菜葉。
我以為我媽會責怪我幾句,或者至少會有些怨言。
出乎意料的是我媽并沒有說什么,也沒有責怪我。
她只是低聲嘆了一句:“唉,也是一條命......”
我忽然涌上來一點莫名的歉意,我問我媽:“你能把它養多久呢?”
當然,與其說這句話是致歉,倒不如說是我宰殺瘸鴨的借口。
我媽并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——她抬起頭,看看比她高出一頭的兒子——也就是拎著瘸鴨的我,慢慢地說:“我就是這樣把你們給盤大的。”
我頓時參悟了我媽此時的全部心境,也知道了我媽嘆息中流露出來的全部含義。
需要解釋一下這個“盤”字。
怎么說呢,它跟“盤古玩”的意思差不多;它跟現在說“盤它”的意思也差不多。
在我老家,“盤”這個方言內涵頗深——當這個字被用在“把孩子盤大”的語境上,一個字就把艱辛拉扯、湊合擺弄、各種哺育、各種陪伴等多種意思,全都給包括進去了。
而在我們家,我媽把我們姐弟三人都給慢慢“盤大了”。
然后我姐姐從故鄉走出來,去了省會城市武漢,很少再回家。
然后我哥哥從故鄉走出來,去了北京,也很少再回家。
而我當時也已經考上了北京的大學,眼見著將來也是不會回故鄉的。
也就是說,這三個被我媽一點一滴盤大的孩子,全都飛出去了,飛出了母親的視野,飛離了母親的空間,但還都還帶著那一條母愛的紐帶。
我媽盤了一輩子的我們,最終盤無可盤。
而這只瘸鴨,卻能讓我媽回憶起那些個盤我們的日日夜夜。
當時我就低下頭嘆了口氣:唉,我真不該殺了這只瘸鴨!
直到現在,母親已經過世好幾年了,這件事依然讓我難以釋懷。